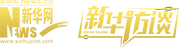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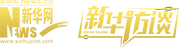


刘世锦:现在房价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特别是年轻人很关心。今年一季度以后,几个一线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和其他一些城市,整个上涨的幅度比较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飙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第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正在推进,但是现在出现了分化。主要是几个大的都市圈,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个大都市圈在加速形成,资源包括人都朝着这些大都市圈集中,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多,这样就产生了需求,对住房的需求是在上升的。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之后出现的正常现象。
第二,和土地制度有关系。这么多年,我们实行的是政府对城市里建设用地独家供应。一家在这控制着土地的供应,没有竞争。而且我们现在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称之为“土地财政”的运营模式,相当多的地区地方财政,卖地的收入构成整个收入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有的地方依赖程度在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既是独家供地,独家垄断,同时让卖地的收入尽可能多。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有些年有些地方供地的速度放缓,有些城市连续几年供地的计划都没有完成,所以一方面需求在上升,供给比较慢,这就造成了房价往上走。
刘世锦: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来讲,2014年构成房地产70%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到1300万套住房。所谓历史需求峰值,就是住房投资最高点,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了,出现了之后,总的趋势就会逐步走平,然后还要逐步下降。到去年9月份之后,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为什么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又开始回升了,最高回升了9%左右。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些限制需求的措施,包括有些地方金融调控加码,一户居民只能买一套房子等限购,这是限制需求。这种措施在短期之内采取一下,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刘世锦:最近一些年我们在推动城市化,但是各级政府事先有一些规划,比如大城市,包括我刚才讲的一线大城市,都是有城镇发展规划的,人口过去可能设想先开始是1000万人,以后是1500万,现在超过2千万了,总得感觉是人口来的太多了。人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实际上是有规律的。全世界,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以后,就会形成几个大的都市圈、都市带,这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所谓的“城市集聚效应”。这种变化实际上超过我们的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去库存,去库存压力最大的就是三四线的城市。比如有一些县城或地级市,过去他们对自己的发展前景预期很高,觉得这个地方将来可能会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的人口,按照那个规模搞建设,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多人来,包括农民进城很多直接到大城市,不一定到这些地方来。一线城市不存在去库存的问题,房子不够。城市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很大程度上和市场的演进是一致的。
刘世锦:房地产税是势在必行。我们过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利用房地产的收益,就是卖地收入。下一步我们要转入到新的、可持续的政府收入机制,这就是房地产税。
三中全会把征收房地产税明确了,现在按照既定的程序逐步推进。这个税收在推进过程中还要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还是要往前推。推了之后,可能对现在过高的房价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地方政府有了一个量相当大、可持续的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来支持城市各方面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刘世锦:中国经济过去6年多是一个回调的态势。从需求的角度来说,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而高投资主要是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高投资要触底,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来看,出口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比重最高的是在2000年左右。最后一只靴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今年一季度之后一线城市房价飙升带动的房地产投资的回升,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过上一段时间之后,房地产投资速度会逐步下降,将来就是一个低速增长,也不排除某个时间会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过去几年我们遇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我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去产能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一方面,我们用一些行政性的办法推动这个事情。市场本身也在做积极的反映。还有一个人们的预期也在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两个指标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就是PPI,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在今年9月份由负转正。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从2014年8月份以后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今年以来也是由负转正,最近一段时间各个行业盈利状况都明显好转。这两个指标显示我们在供给侧方面也是接近底部了。
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由过去高速增长的供求关系向中速增长供求关系的调整已经接近底部了。当然接近触底和真正触底是两回事,今后一两年有很大的可能会实现触底。但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会超出以往,我们要关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
刘世锦: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房地产,泡沫是否会破灭?金融风险是否能得到有效控制?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因素。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否正确处置,来应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或者风险因素的冲击?
争取今后一两年中国经济能够平稳触底,触底以后进入这样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这个平台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应该是能够保持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应该就会有一个得以实现的比较好的基础。
刘世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些短期的任务,也有一些中长期的任务。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战场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所谓要素市场,就是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这些要素,让它们市场化。
我们有一些行业,特别是基础行业,还是存在所谓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这个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我们一些基础产业领域,比如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铁路、金融等等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这些方面的问题。
比如电信市场,我们现在最大的是中国移动,还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应该说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但是消费者还是感觉到资费比较高,一直呼吁要降低资费。但是大家又感觉到在目前这种市场格局下,降低资费很困难。为什么呢?是你让它降资费,而不是它自己要降资费。现在IT产业一些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进入一两个民营企业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适度竞争一下,资费一定会下来。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电信用户,理应成为全世界资费最低的地方。这个领域还是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这是什么改革呢?这就是供给侧的改革。
刘世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的好不好,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是否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有人觉得中国这几年经济不会好,是L型低迷状态,我想说,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
因为中国经济将来保持一个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是稳定的、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没有水分,有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样一个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确实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L型不是一个低迷、消极的增长状态,它是符合规律的、正常的,而且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之后成为一个没有水分,有质量、有效益、稳得住、可持续的增长平台。这是我们今后几年要努力争取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成功不成功、是不是取得预期成果的一个验证的标的物或者说一个目标。